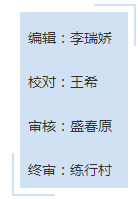试论抗疫时代的戏剧如何逆行
发布时间:2022-04-02 作者:本站 来源:中国粤剧网 点击:
广播剧与“幻境新歌”的逆行
从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现场观剧成为了困难。剧场转入网络和电台媒体寻求发展,涌现出一批以抗疫为主题的广播剧作品,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播出的《逆行者》、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栏目组推出的《北京防疫一家人(系列剧)》《但愿人长久(纪实剧)》、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出品的《你好我的城》、深圳制作的《大爱无疆》《梦醒花开》、温州广电传媒集团出品的《果果的抗疫日记(儿童广播剧)》、南宁交通广播出品的《抗疫系列》、广州广播电台出品的《轻松抗疫一家亲》、佛山演艺中心携手佛山电台FM98.5花花剧场联合打造的抗疫广播剧《共情》(粤语播出)、由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首播的《新房》(普通话播出)等,都在各大平台上重新引起老戏迷的关注和新戏迷的热搜,让这两年的戏剧圈不太冷。

抗疫广播剧《共情》海报
这些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广播剧,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艺术成品的质量,大多与剧本自身扎实的话剧底本或文学底本分不开,不少广播剧作品的前身就是比较成熟的话剧作品、文学作品、纪实作品,而从事改编的不少也是话剧编剧或文学作者本人,这就使得整个创作、改编的过程在戏剧风格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如在佛山地区引起热议的广播剧《共情》和《新房》,其作者便是活跃的话剧编剧猫青、多栖编剧尹洪波和资深的文学作者及研究者杨凡周。广播剧的重新出现,似乎让戏剧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在广播剧家庭里面,如果说话剧还能占半壁江山,那戏曲的位置在哪里呢?戏曲文体的作品,多见于舞台,在电台广播中则不多见。耳畔所闻多是只说不唱的说书、讲古,或是侧重清唱的曲艺文体,如各类评弹、鼓子书等,结构均较为单一。很少看到有针对电台制作的戏曲广播剧类型的作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粤曲界曾有过一种试验性质的曲艺剧“幻境新歌”,打破了粤曲由角色独唱、对唱、联唱的单纯音乐结构,大幅增加了说话艺术,即角色的代言体对白和第三者的叙事体旁白,并尝试融入演出艺术,也就是让唱家在舞台上带妆设景演出。这样一来,篇幅从原来一折扩充至几场连缀的完整结构,与粤剧的演出形式已十分相似。粤剧舞台经过了现代衍变,在戏剧结构上已经从传奇文学的连载多场结构转向中短篇的元杂剧、话剧、歌剧等方面对齐,在剧本的写作上,已经很少见到古老戏曲中报家门、背供、帮腔这些叙述体的补充,也少了过渡场次对剧情的补充说明、对次要人物的刻画丰富,整体上人少、话短、戏紧、唱多,更强调剧场的既视感、现场感,主要针对一次性消费的剧场。但以听觉和回忆、想象为核心的文学系统,包括以文字为主的雅文学和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民间文学,尤其是说话文学,它们的特点则是人多、话长、戏慢,主要针对连续性消费或间歇性消费的需要,因而造就了传奇体裁和连载说话体裁,并且在观赏体验上主要以“听戏”为主。过去我们为什么不说看戏,而说听戏,除了当中有大量的唱段和唱功的表现之外,自然不能忽视的是当中说话艺术及其内容的重要作用。“幻境新歌”之所以说特别,在于它不仅重新恢复了“曲+说+演”相结合的古老戏曲体验,并且更在其结构中增加了旁述者这一角色,在各场间隙或演出进程中对场中角色的背景、身份、历史、正在进行的事件、心理活动及即将出场的人物、事件进行及时的说明,当然,也善于制造悬念和回忆,这其实就相当于说话艺人在故事演绎中的叙述身份了。这种演出主要是适应了当时茶居茶座等消费场所表演空间不大、表演资金不多的限制,采取了有限度的彩唱和戏曲演技展示,并突出了多维度的听觉欣赏的特点。在整个过程中,不仅保留与粤剧相似的完整的故事、人物,并且还将之进一步的文学化复原,以娓娓道来的说话艺术作为基底,在保留核心唱段的同时将整个故事架构拉长、拉松,从而让茶客存有回忆和追求的空间,恰如茶客间每天的约定。但可惜,这种实验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事者也不多,在当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或许是因为文学改编难而单曲演唱易的缘故吧,相对而言演出费用高而受益低,演唱费用低而受益高,茶居茶座毕竟也处于强弩之末,不复当年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粤剧编剧王建勋曾以歌伶小明星的故事创作“幻境新歌”版的曲艺剧《风流梦》,此后无人续弦。
戏曲的听戏时代能否重现
2019年由高志森导演、著名曲艺唱家梁玉嵘、谐星黄俊英及一众曲艺、话剧表演家担纲的曲艺剧《小明星》在广佛舞台亮相,仿佛让人重新看到“幻境新歌”的掠影,看到听戏时代回归的希望。但将这种本该放置于听觉欣赏为主的消费场所的艺术样式放在了大剧场演出,其特色和得失比在茶居茶座中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特色方面,因为在剧本写作中借鉴了“幻境新歌”的写作方式,所以在整体结构上自然也更倚重唱家的演唱技巧和核心唱段的编排,全剧说、演的任务主要通过原本戏曲中的丑或话剧中的谐星来调动,从而完成全剧冷热场的分配和穿织调节问题。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使这个更倾向于听觉的作品立于大舞台?因此剧团邀请了香港春天舞台的高志森来做导演。高志森善于导演具有怀旧叙述风格的话剧,深谙传统戏曲当中的说话艺术和叙述视觉,从而能够以话剧为地基较好的架构起传统风格与现代风格融合的作品,屡屡制作出话剧界、粤剧界、歌舞剧界、文学界跨界合作的作品,如谢君豪的《南海十三郎》《梁祝》系列、《一代天娇红线女》《小明星》等名唱家剧场、《长恨歌》等名作家剧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时装舞剧剧场《功夫少年》等武术剧场。以上这些,无不扎根于传统文学,尤其是传统连载式的说话文学,整体架构上都是较为散而淡,充满回忆的味道,和当下注重效益的剧场既视感和紧凑感很不一样。但情怀归情怀,艺术是艺术。高志森这类作品能够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能否让观众进入到他所设计的文学想象空间和融入了自身体验的回忆空间中,如果观众仅仅按照严格的舞台欣赏经验,着眼于台上的表演和场面所带来的真实性感受,怕是会觉得简陋,也感到失望。但如果为了照顾场面上美轮美奂,营造更为真实的舞台,会不会又压缩了由文学带来的虚拟的、情感的、回忆的空间呢?近现代话剧往往就是在这两难中徘徊,一方面继承了古老说话艺术的特点,但却因西方话剧的渗透而逐渐失去虚拟、情感、回忆、文学的特点(这也许就是为何契科夫散文剧受到当代剧人反思的原因)。这恐怕是很难取舍的。因而我觉得在一个较小的剧场内欣赏听觉类的艺术样式,是比较恰当的,整体上也无需过分花哨,重点应该放在文学方面。因而,也更能够适应改编为广播剧,与现代媒体技术结合的契机,为未来打开一条通道。


曲艺剧《小明星》海报
像“幻境新歌”和曲艺剧《小明星》这类新剧,从艺术形式成熟的角度上来看自然未算尽善尽美,但鉴于“十分适合电台、唱碟和网络媒体来播放的大戏”实在太过缺乏,更缺乏持续性的研究和发展,所以这条在戏曲现代舞台戏探索之外,通过曲艺和说话艺术结合以取得更广泛的“广播效果”的道路还是值得珍视的。这次疫情让戏剧界有了一次大战前夕的感受,戏曲有没有一个比现在更普适的形式,有没有一个能诉诸于听觉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形式来获取更多人群的接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听戏时代能否全面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这个问题还有待有心人去解开。路人茫茫临歧路,晨星依旧在东方。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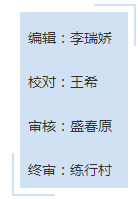
从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现场观剧成为了困难。剧场转入网络和电台媒体寻求发展,涌现出一批以抗疫为主题的广播剧作品,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播出的《逆行者》、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栏目组推出的《北京防疫一家人(系列剧)》《但愿人长久(纪实剧)》、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出品的《你好我的城》、深圳制作的《大爱无疆》《梦醒花开》、温州广电传媒集团出品的《果果的抗疫日记(儿童广播剧)》、南宁交通广播出品的《抗疫系列》、广州广播电台出品的《轻松抗疫一家亲》、佛山演艺中心携手佛山电台FM98.5花花剧场联合打造的抗疫广播剧《共情》(粤语播出)、由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首播的《新房》(普通话播出)等,都在各大平台上重新引起老戏迷的关注和新戏迷的热搜,让这两年的戏剧圈不太冷。

抗疫广播剧《共情》海报
戏曲的听戏时代能否重现
2019年由高志森导演、著名曲艺唱家梁玉嵘、谐星黄俊英及一众曲艺、话剧表演家担纲的曲艺剧《小明星》在广佛舞台亮相,仿佛让人重新看到“幻境新歌”的掠影,看到听戏时代回归的希望。但将这种本该放置于听觉欣赏为主的消费场所的艺术样式放在了大剧场演出,其特色和得失比在茶居茶座中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特色方面,因为在剧本写作中借鉴了“幻境新歌”的写作方式,所以在整体结构上自然也更倚重唱家的演唱技巧和核心唱段的编排,全剧说、演的任务主要通过原本戏曲中的丑或话剧中的谐星来调动,从而完成全剧冷热场的分配和穿织调节问题。但问题随之而来,如何使这个更倾向于听觉的作品立于大舞台?因此剧团邀请了香港春天舞台的高志森来做导演。高志森善于导演具有怀旧叙述风格的话剧,深谙传统戏曲当中的说话艺术和叙述视觉,从而能够以话剧为地基较好的架构起传统风格与现代风格融合的作品,屡屡制作出话剧界、粤剧界、歌舞剧界、文学界跨界合作的作品,如谢君豪的《南海十三郎》《梁祝》系列、《一代天娇红线女》《小明星》等名唱家剧场、《长恨歌》等名作家剧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时装舞剧剧场《功夫少年》等武术剧场。以上这些,无不扎根于传统文学,尤其是传统连载式的说话文学,整体架构上都是较为散而淡,充满回忆的味道,和当下注重效益的剧场既视感和紧凑感很不一样。但情怀归情怀,艺术是艺术。高志森这类作品能够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能否让观众进入到他所设计的文学想象空间和融入了自身体验的回忆空间中,如果观众仅仅按照严格的舞台欣赏经验,着眼于台上的表演和场面所带来的真实性感受,怕是会觉得简陋,也感到失望。但如果为了照顾场面上美轮美奂,营造更为真实的舞台,会不会又压缩了由文学带来的虚拟的、情感的、回忆的空间呢?近现代话剧往往就是在这两难中徘徊,一方面继承了古老说话艺术的特点,但却因西方话剧的渗透而逐渐失去虚拟、情感、回忆、文学的特点(这也许就是为何契科夫散文剧受到当代剧人反思的原因)。这恐怕是很难取舍的。因而我觉得在一个较小的剧场内欣赏听觉类的艺术样式,是比较恰当的,整体上也无需过分花哨,重点应该放在文学方面。因而,也更能够适应改编为广播剧,与现代媒体技术结合的契机,为未来打开一条通道。

曲艺剧《小明星》海报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