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莲悲遭劫,白玉叹蒙尘——评陈冠卿一部被忽视的佳作《洛水神仙》(下)
发布时间:2018-10-19 作者:包子店长 来源:中国粤剧网 点击:
(接上文)
新编历史“神话”剧
在1981年油印剧本的封面上,除了印着“洛神”的剧名大字外,还有一行小字:新编历史神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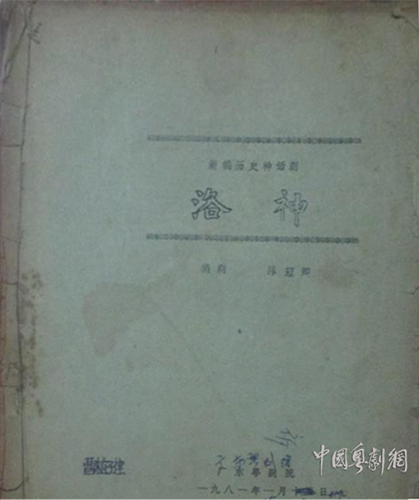
1981年油印剧本《洛神》封面
说“新编”“历史”都好理解,可是“神话”?难道是说最后不足十分钟的子建遇洛神?这可就有意思了。
陈冠卿编撰《洛水神仙》很多细节都有史可考。比如玉缕金带枕(唐涤生版《洛神》作“金缕玉带枕”)出自唐代李善注引《汉书音义》,亦如其中所述设定为甄氏未嫁时所有,而不是像《子建会洛神》一样由曹操所赐。此外也设定子建“求甄逸女,既不遂”,至于历史上甄氏早在建安九年就嫁为曹氏所得这个矛盾,剧中就以“甄逸在曹操讨袁绍时献计有功,获赐黄金白玉,与女归隐田园,然后玉婵与曹家兄弟分别相识”来解决。《白马篇》的写作和曹植受封临淄侯的时间,按照历史定为建安十六年;到经过洛水、将要写下《洛神赋》时,又按曹植其时的封号,随从对他的称呼从“侯爷”改为“王爷”。剧中阴险狡诈的反派华歆,在历史上曾被管宁“割席断交”;在临淄与子建诗酒唱和的丁仪、丁异(廙)兄弟,历史上也是曹植的友人。
所以,“神话”在何处呢?
曹植与甄氏(洛神)的爱情故事自《洛神赋》而来,《洛神赋》有一句序言,言明曹植的写作动机: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宋玉在《神女赋》中极写神女的美丽与神圣,然而襄王有意,神女无心,这番仰慕最终都是一场空。曹植借用了这一体裁,以他与洛川水神相会的经历写成《洛神赋》——神女是神话,洛神自然也是神话。古人素有以美人香草喻君臣大义的传统,这种象征手法始创于屈原,有明显的楚地文化特征,也为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所共鸣。所以不管是《神女赋》还是《洛神赋》,在美人香草的外衣之下,都有作者的寄托。
陈冠卿在《洛水神仙》中也有他的寄托。对比他其后数年创作的《梦断香销四十年》,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之间有微妙的相似:男主角都是怀揣从军报国志向的豪放派诗人;男女主角志同道合而女主角都为了成全男主角的志向而选择牺牲个人幸福;男主角被怀疑、被诬陷,满腔抱负付诸东流;女主角另外成婚后,与男主角在酒宴上相逢,女主角奉给男主角一杯酒,从此两人分隔天涯;女主角在与男主角见面后郁郁寡欢,在“世情薄、人情恶”之中念诵着男主角的诗文病逝;多年后,男主角凭吊旧物/旧地,在朦胧中再次见到女主角。
“既伤国,复伤情”是《梦断香销四十年》里陆游形象的注释,伤国与伤情,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为表,亦为里。《洛水神仙》中也有相似的一段,来自曹植的自述:
临风雪涕,叶离离,枝曳曳,飘零已惯,休问转篷桅,伤情莫过佳人弃我如遗。热泪洒离觞,满腔愁愤入东齐。沧海起悲风,惊闻父王去逝。爹爹,父王,你功未成身先死啊……抚膺痛,骨肉相残如水火,我宝剑难挥。曹子建,报国有心,屡遭钳制;赢得是,虚文一纸,权领东齐。今已矣,今已矣,惟有弹剑高歌,抒我怀,悲乱世。正是诗酒剑琴为我伴,休再念缕金枕上别人妻。
陈冠卿编撰《洛水神仙》很多细节都有史可考。比如玉缕金带枕(唐涤生版《洛神》作“金缕玉带枕”)出自唐代李善注引《汉书音义》,亦如其中所述设定为甄氏未嫁时所有,而不是像《子建会洛神》一样由曹操所赐。此外也设定子建“求甄逸女,既不遂”,至于历史上甄氏早在建安九年就嫁为曹氏所得这个矛盾,剧中就以“甄逸在曹操讨袁绍时献计有功,获赐黄金白玉,与女归隐田园,然后玉婵与曹家兄弟分别相识”来解决。《白马篇》的写作和曹植受封临淄侯的时间,按照历史定为建安十六年;到经过洛水、将要写下《洛神赋》时,又按曹植其时的封号,随从对他的称呼从“侯爷”改为“王爷”。剧中阴险狡诈的反派华歆,在历史上曾被管宁“割席断交”;在临淄与子建诗酒唱和的丁仪、丁异(廙)兄弟,历史上也是曹植的友人。
所以,“神话”在何处呢?
曹植与甄氏(洛神)的爱情故事自《洛神赋》而来,《洛神赋》有一句序言,言明曹植的写作动机: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宋玉在《神女赋》中极写神女的美丽与神圣,然而襄王有意,神女无心,这番仰慕最终都是一场空。曹植借用了这一体裁,以他与洛川水神相会的经历写成《洛神赋》——神女是神话,洛神自然也是神话。古人素有以美人香草喻君臣大义的传统,这种象征手法始创于屈原,有明显的楚地文化特征,也为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所共鸣。所以不管是《神女赋》还是《洛神赋》,在美人香草的外衣之下,都有作者的寄托。
陈冠卿在《洛水神仙》中也有他的寄托。对比他其后数年创作的《梦断香销四十年》,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之间有微妙的相似:男主角都是怀揣从军报国志向的豪放派诗人;男女主角志同道合而女主角都为了成全男主角的志向而选择牺牲个人幸福;男主角被怀疑、被诬陷,满腔抱负付诸东流;女主角另外成婚后,与男主角在酒宴上相逢,女主角奉给男主角一杯酒,从此两人分隔天涯;女主角在与男主角见面后郁郁寡欢,在“世情薄、人情恶”之中念诵着男主角的诗文病逝;多年后,男主角凭吊旧物/旧地,在朦胧中再次见到女主角。
“既伤国,复伤情”是《梦断香销四十年》里陆游形象的注释,伤国与伤情,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为表,亦为里。《洛水神仙》中也有相似的一段,来自曹植的自述:
临风雪涕,叶离离,枝曳曳,飘零已惯,休问转篷桅,伤情莫过佳人弃我如遗。热泪洒离觞,满腔愁愤入东齐。沧海起悲风,惊闻父王去逝。爹爹,父王,你功未成身先死啊……抚膺痛,骨肉相残如水火,我宝剑难挥。曹子建,报国有心,屡遭钳制;赢得是,虚文一纸,权领东齐。今已矣,今已矣,惟有弹剑高歌,抒我怀,悲乱世。正是诗酒剑琴为我伴,休再念缕金枕上别人妻。
——《洛水神仙 第四场 劝归》

《洛水神仙》DVD碟封面
洛神的故事虽来自曹植的《洛神赋》,但《洛水神仙》的题眼却落在《白马篇》与《怨歌行》。在第六场“伤逝”中有一句曲词: 白马篇,怨歌行,有志不能伸,见疑枉推心。
既概括了《洛水神仙》中的子建,也概括了玉婵的一生。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视己身为“壮士”,可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报国的热忱当中。可是现实给予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纯真敌不过世故,诚挚敌不过多疑,越是才华横溢、天纵骄姿,越是不可见容于世。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既概括了《洛水神仙》中的子建,也概括了玉婵的一生。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视己身为“壮士”,可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报国的热忱当中。可是现实给予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纯真敌不过世故,诚挚敌不过多疑,越是才华横溢、天纵骄姿,越是不可见容于世。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曹植《怨歌行》
尽管有怨,尽管有恨,但在最抑郁不得志时,子建仍是慷慨激昂,弹剑而歌;在最悲伤绝望之际,玉婵还是忠贞自守,以家国为念。风骨,气节,无论如何困难、艰苦,都是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始终应该坚守的骄傲。陈冠卿还坚守着文人的风骨和气节,只是这份古典情怀却越来越少人会懂得。
红莲悲遭劫,白玉叹蒙尘
电影《南海十三郎》有一段情节:抗战胜利后,戏行恢复繁荣,但南海十三郎那些反映战争苦难以及促人爱国、抗争、奋进的剧本却受到冷遇,剧院经理说“现在观众见到打仗就害怕”。虽然年代相距数十年,但《洛水神仙》遭遇的困境未尝不相似。时间进入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观众更愿意欣赏的,是一些更具娱乐性的剧目,故事浅显易懂,不需要较高端知识水平——更遑论要去理解合该被历史淘汰的士大夫情怀。
于是《洛水神仙》,后来就被改成了《洛水情梦》。“泪宴”上玉婵不再对曹丕横眉冷对,曹丕在“赋诗”时就已经登基;玉婵不曾患病,也没有“辞枕”,早在铜雀台上她就已经投水身死——空有“白马”,不留“怨歌”,连最后的“会洛”都被换上一首香港粤曲《洛水梦会》。那个金戈铁马、弹剑高歌的曹子建不存在了,剩下的是哀叹“可怜我在人间受苦,求你引渡”的一介凡夫;那个贞烈高洁、襟怀宽广的甄玉婵也不存在了,只有夙愿是“为才郎叠被铺床”仅求安身立命幸福生活的寻常女子。
这个故事,重新又变成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和另一个老旧版本的《洛神》一起,成为我们现在时常得见的粤剧演出剧目。
实际上,曹植的《怨歌行》作于魏明帝(曹丕之子)时代,本不可能在剧中的时间线出现。所以陈冠卿也不像《白马篇》一样直接引用,只是化用了当中句子,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与寄托。而恰恰正是《怨歌行》,好似又正好成为了《洛水神仙》命运的注脚:
忠信事不显,乃见有疑患。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于是《洛水神仙》,后来就被改成了《洛水情梦》。“泪宴”上玉婵不再对曹丕横眉冷对,曹丕在“赋诗”时就已经登基;玉婵不曾患病,也没有“辞枕”,早在铜雀台上她就已经投水身死——空有“白马”,不留“怨歌”,连最后的“会洛”都被换上一首香港粤曲《洛水梦会》。那个金戈铁马、弹剑高歌的曹子建不存在了,剩下的是哀叹“可怜我在人间受苦,求你引渡”的一介凡夫;那个贞烈高洁、襟怀宽广的甄玉婵也不存在了,只有夙愿是“为才郎叠被铺床”仅求安身立命幸福生活的寻常女子。
这个故事,重新又变成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和另一个老旧版本的《洛神》一起,成为我们现在时常得见的粤剧演出剧目。
实际上,曹植的《怨歌行》作于魏明帝(曹丕之子)时代,本不可能在剧中的时间线出现。所以陈冠卿也不像《白马篇》一样直接引用,只是化用了当中句子,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与寄托。而恰恰正是《怨歌行》,好似又正好成为了《洛水神仙》命运的注脚:
忠信事不显,乃见有疑患。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全文完)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中国粤剧网为推广粤剧,以予刊载,特此声明。


